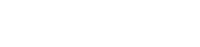朝廷众臣怎么都没有料到,皇太女的册封诏书尚未颁发,关于皇太女学习教材的制定就广诏世人了。
“荒唐,简直不要太荒唐了!”
都察院御史涂文仁气得直奔典籍厅,见了首辅言远,当即激情输出:
“首辅大人,从古至今,储君之师不是享誉世间的大儒担任,就是由您这样的朝廷重臣负责,何曾听说过广纳天下之意见,不分达者和黔首?
下官也是出自民间,最是清楚那些目不识丁者的愚昧,难不成皇上连刁民意见也要采纳?!
难不成,那群贩夫走卒、丐疍户者也有资格对储君的教导上指手画脚?他们也配呢!”
说到激动时,涂文仁气得顿足捶胸,浊泪涟涟:“言首辅,您是百臣之首、朝廷砥柱,万不能看着皇上这般行事!这样下去,皇储威严何存?难不成我们的储君凭谁都能指指点点评头论足?!”
要不是还有几分理智,他此刻都要高喝一声“圣上糊涂”了!
饶是这样,面色略沉的言远还是低声制止了他:“涂御史!作为臣子,你能为社稷江山考虑、为圣上皇储考量,这很好,可任凭你一片赤诚之心,也不能忘记尊卑,有些话不是当臣子可以说的。”
涂文仁的胸脯上下起伏激烈,好半晌才把不平之气放缓。
“首辅教导的是,是下官考虑不周,可……”想到那份面向天下人的征求意见诏书,涂文仁就气得想要暴走,忍来忍去仍旧忍无可忍的他,一拳捣在旁边儿的桌面上,恨声说,“以下官之见,能想出这等闻所未闻的主意的,除了那个盛文臻不会再有旁人!至少和她有关!”
他这话说的,向来好脾气的言远都无语了。
一直站在书架前的次辅古蕴程则笑出了声:“涂御史,你这般说可有证据?若是没有,当心盛侍郎知晓了,反而要告你个无端污蔑之错!”
不远处径自研磨的岑闽舟也没忍住,头都没抬的冷笑了两声,才语调上扬的说着风凉话:“涂御史曾领教过她的刁蛮吧?怎地这么快就忘了?凡事要有证据!空口而谈,这有何用?”
涂文仁听他俩说话,脑袋一会儿转向次辅这边儿,一会儿转向了三辅那边儿,听到最后却不气馁,言之凿凿地说:“此想法非下官一人所有,都察院、通政司、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国子监、六科者,皆有许多不赞成者,大家都已摩拳擦掌,不日就要就此诏书问题作出弹劾!更有不少人准备联名奏告盛文臻!”
言远眯了眯眼,打量着义愤填膺的涂文仁,双指扣着桌面好半晌,才问他:“涂御史今日来寻老夫,是想老夫做什么呢?”
“大人,下官想请您代领吾等臣子,一起劝谏圣上三思!”
涂文仁的要求听着不算无礼,这本也是首辅应有的职责之一,可言远此刻却不想应承。
“涂御史,你说的是劝谏,还是聚力胁迫?”
岑闽舟见言远眸色发沉,登时出声提醒:“首辅带领百官协助皇上治国,于政事上替君分忧、于政令上提供意见、于朝事上查漏补缺……皆是职责所在,可这不等于首辅大人能带着朝臣强迫皇上朝令夕改!老夫这人素来直爽,说句不好听的,涂御史你找的不是言首辅,是那等恨不能把持朝政的奸臣权相呢!”
“三辅大人慎言!”涂御史闻此言,勃然色变地站了起来,“此话怎可轻易所言?!下官一片为朝廷为社稷为皇储的赤诚,怎么就和那乱臣贼子挂上钩了?!”
古蕴程见他恼怒,轻笑:“涂御史何必这样惊恼?岑三辅话说得虽然直,可他的话却不偏呢!你只觉得此言不大好听,却怎么不想想,若真让你按设想做成了,事儿可就难办了!之后的影响、结果也不可能好看!”
“下、下官……”涂文仁红着脸,踟蹰着缓缓地收了脾气,不过,他的想法儿却没改变太多,“就算内阁诸位大人都不肯劝谏,吾和其他志同道的同僚也要上疏皇上!”
“劝谏圣上,此乃都察院之职责、是你们御史的工作、更是每个朝臣的义务。”言远颔首,不曾反对。
眼见请不到首辅言远,而旁边儿的次辅、三辅,看样子也不乐意掺合,涂文仁颓然长叹了一声,这才满不是滋味的拱手离开。
“怎么样!涂兄,首辅他们怎么说呢?”
离开典籍厅,涂文仁才刚出衙署大门,就让各部的同僚给围了起来。
“诸位,劝谏之事,只怕要靠吾等自己了!”涂文仁悲愤的晃了晃头。
顿时,刚刚还议论热闹的场面安静了下来。
更有不少官员悄悄地往人群外退去。
“要吾说,咱们就该寻盛文臻辩论去!”
此言一出,很多人循声环首,带看清说话者是通政使司通政,登时了然:怪不得着重提盛文臻的,原来这位和她有龃龉呢!
“郑通政,虽说咱们猜测此诏和她盛文臻有关,可咱没有证据,这般情况,怎好和她辩论?那盛文臻满可以不搭理咱们!”
“恰恰相反呢!”郑通政抚着胡子,智珠在握的朝对方晃了晃脑袋,“且不说此诏令有没有她盛文臻的手笔,但凡她支持此诏书,定然就会维护!所以为了诏令可以施行,她也要接了咱们的邀约。”
“若此政令非出自她手,而她对此亦是不大赞成呢?”
郑通政闻声,不约而同的和涂文仁循声找寻,可惜周围的人太多了,说话的那位又只说一句,故而寻了半晌亦没寻到说话人,只好胸有成竹地对外表示:“此诏事关太女,皇后对此亦是支持,故而不管盛文臻人后怎么和皇后公主说,人前,她定然会维护诏令的!”
“可咱上疏之目的,是希望皇上修改诏令,不是一味地和盛文臻相斗啊!”
此人这话说完,一阵小声议论之后,又有许多官员悄声离开。
没办法,他们准备劝谏皇上收回诏令,是因为此乃他们的职责和目的。
盛文臻只是可能出现得一个障碍,拦着他们了,将其搬开就是。
若是人家没有出现,他们也不能把人搬过去充障碍,然后再绞尽脑汁琢磨怎么对付她。
毕竟,他们目的可不是搬倒盛文臻。
“荒唐,简直不要太荒唐了!”
都察院御史涂文仁气得直奔典籍厅,见了首辅言远,当即激情输出:
“首辅大人,从古至今,储君之师不是享誉世间的大儒担任,就是由您这样的朝廷重臣负责,何曾听说过广纳天下之意见,不分达者和黔首?
下官也是出自民间,最是清楚那些目不识丁者的愚昧,难不成皇上连刁民意见也要采纳?!
难不成,那群贩夫走卒、丐疍户者也有资格对储君的教导上指手画脚?他们也配呢!”
说到激动时,涂文仁气得顿足捶胸,浊泪涟涟:“言首辅,您是百臣之首、朝廷砥柱,万不能看着皇上这般行事!这样下去,皇储威严何存?难不成我们的储君凭谁都能指指点点评头论足?!”
要不是还有几分理智,他此刻都要高喝一声“圣上糊涂”了!
饶是这样,面色略沉的言远还是低声制止了他:“涂御史!作为臣子,你能为社稷江山考虑、为圣上皇储考量,这很好,可任凭你一片赤诚之心,也不能忘记尊卑,有些话不是当臣子可以说的。”
涂文仁的胸脯上下起伏激烈,好半晌才把不平之气放缓。
“首辅教导的是,是下官考虑不周,可……”想到那份面向天下人的征求意见诏书,涂文仁就气得想要暴走,忍来忍去仍旧忍无可忍的他,一拳捣在旁边儿的桌面上,恨声说,“以下官之见,能想出这等闻所未闻的主意的,除了那个盛文臻不会再有旁人!至少和她有关!”
他这话说的,向来好脾气的言远都无语了。
一直站在书架前的次辅古蕴程则笑出了声:“涂御史,你这般说可有证据?若是没有,当心盛侍郎知晓了,反而要告你个无端污蔑之错!”
不远处径自研磨的岑闽舟也没忍住,头都没抬的冷笑了两声,才语调上扬的说着风凉话:“涂御史曾领教过她的刁蛮吧?怎地这么快就忘了?凡事要有证据!空口而谈,这有何用?”
涂文仁听他俩说话,脑袋一会儿转向次辅这边儿,一会儿转向了三辅那边儿,听到最后却不气馁,言之凿凿地说:“此想法非下官一人所有,都察院、通政司、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国子监、六科者,皆有许多不赞成者,大家都已摩拳擦掌,不日就要就此诏书问题作出弹劾!更有不少人准备联名奏告盛文臻!”
言远眯了眯眼,打量着义愤填膺的涂文仁,双指扣着桌面好半晌,才问他:“涂御史今日来寻老夫,是想老夫做什么呢?”
“大人,下官想请您代领吾等臣子,一起劝谏圣上三思!”
涂文仁的要求听着不算无礼,这本也是首辅应有的职责之一,可言远此刻却不想应承。
“涂御史,你说的是劝谏,还是聚力胁迫?”
岑闽舟见言远眸色发沉,登时出声提醒:“首辅带领百官协助皇上治国,于政事上替君分忧、于政令上提供意见、于朝事上查漏补缺……皆是职责所在,可这不等于首辅大人能带着朝臣强迫皇上朝令夕改!老夫这人素来直爽,说句不好听的,涂御史你找的不是言首辅,是那等恨不能把持朝政的奸臣权相呢!”
“三辅大人慎言!”涂御史闻此言,勃然色变地站了起来,“此话怎可轻易所言?!下官一片为朝廷为社稷为皇储的赤诚,怎么就和那乱臣贼子挂上钩了?!”
古蕴程见他恼怒,轻笑:“涂御史何必这样惊恼?岑三辅话说得虽然直,可他的话却不偏呢!你只觉得此言不大好听,却怎么不想想,若真让你按设想做成了,事儿可就难办了!之后的影响、结果也不可能好看!”
“下、下官……”涂文仁红着脸,踟蹰着缓缓地收了脾气,不过,他的想法儿却没改变太多,“就算内阁诸位大人都不肯劝谏,吾和其他志同道的同僚也要上疏皇上!”
“劝谏圣上,此乃都察院之职责、是你们御史的工作、更是每个朝臣的义务。”言远颔首,不曾反对。
眼见请不到首辅言远,而旁边儿的次辅、三辅,看样子也不乐意掺合,涂文仁颓然长叹了一声,这才满不是滋味的拱手离开。
“怎么样!涂兄,首辅他们怎么说呢?”
离开典籍厅,涂文仁才刚出衙署大门,就让各部的同僚给围了起来。
“诸位,劝谏之事,只怕要靠吾等自己了!”涂文仁悲愤的晃了晃头。
顿时,刚刚还议论热闹的场面安静了下来。
更有不少官员悄悄地往人群外退去。
“要吾说,咱们就该寻盛文臻辩论去!”
此言一出,很多人循声环首,带看清说话者是通政使司通政,登时了然:怪不得着重提盛文臻的,原来这位和她有龃龉呢!
“郑通政,虽说咱们猜测此诏和她盛文臻有关,可咱没有证据,这般情况,怎好和她辩论?那盛文臻满可以不搭理咱们!”
“恰恰相反呢!”郑通政抚着胡子,智珠在握的朝对方晃了晃脑袋,“且不说此诏令有没有她盛文臻的手笔,但凡她支持此诏书,定然就会维护!所以为了诏令可以施行,她也要接了咱们的邀约。”
“若此政令非出自她手,而她对此亦是不大赞成呢?”
郑通政闻声,不约而同的和涂文仁循声找寻,可惜周围的人太多了,说话的那位又只说一句,故而寻了半晌亦没寻到说话人,只好胸有成竹地对外表示:“此诏事关太女,皇后对此亦是支持,故而不管盛文臻人后怎么和皇后公主说,人前,她定然会维护诏令的!”
“可咱上疏之目的,是希望皇上修改诏令,不是一味地和盛文臻相斗啊!”
此人这话说完,一阵小声议论之后,又有许多官员悄声离开。
没办法,他们准备劝谏皇上收回诏令,是因为此乃他们的职责和目的。
盛文臻只是可能出现得一个障碍,拦着他们了,将其搬开就是。
若是人家没有出现,他们也不能把人搬过去充障碍,然后再绞尽脑汁琢磨怎么对付她。
毕竟,他们目的可不是搬倒盛文臻。